

您访问的链接即将离开“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是否继续?
继续访问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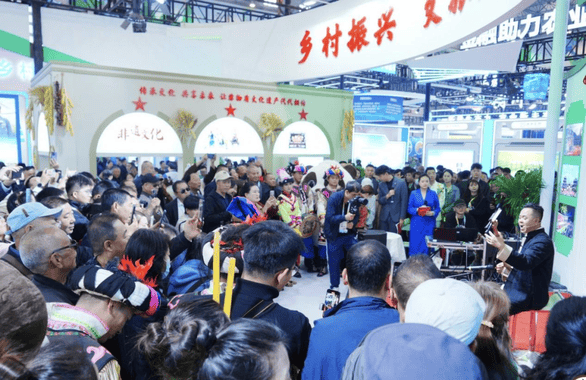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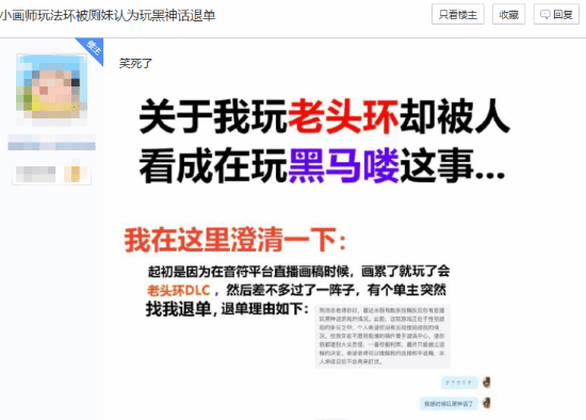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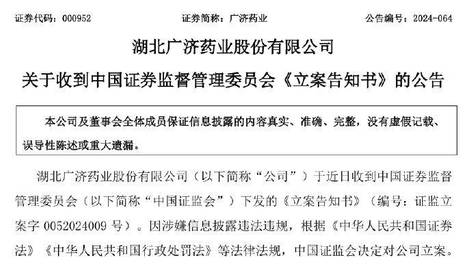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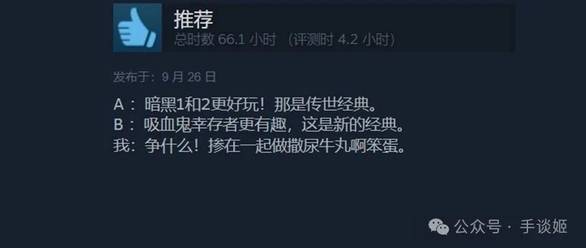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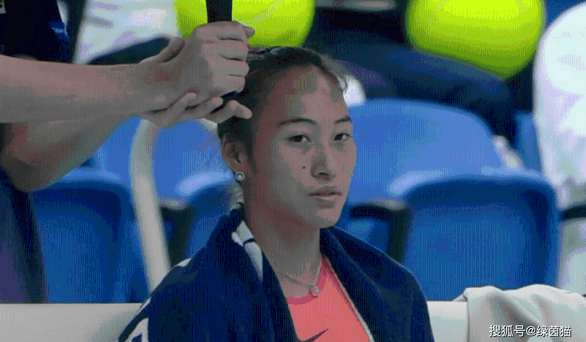 19109
19109
 87
2025-05-15 03:32:18
87
2025-05-15 03:32:18



 62496
62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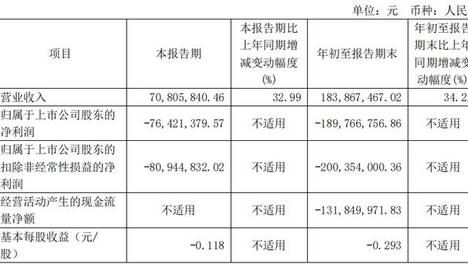 74
2025-05-15 03:32:18
74
2025-05-15 03:32:18



 20131
20131
 89
2025-05-15 03:32:18
89
2025-05-15 03:32:18



 41813
41813
 20
2025-05-15 03:32:18
20
2025-05-15 03:32:18



 67517
67517
 31
2025-05-15 03:32:18
31
2025-05-15 03:32:18



 45432
45432
 24
2025-05-15 03:32:18
24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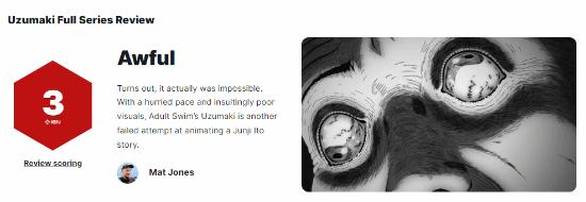


 17263
17263
 71
2025-05-15 03:32:18
71
2025-05-15 03:32:18



 79469
79469
 48
2025-05-15 03:32:18
48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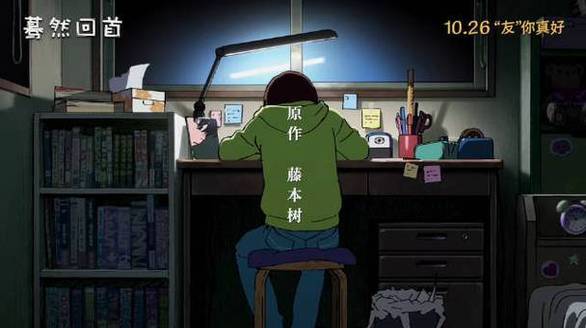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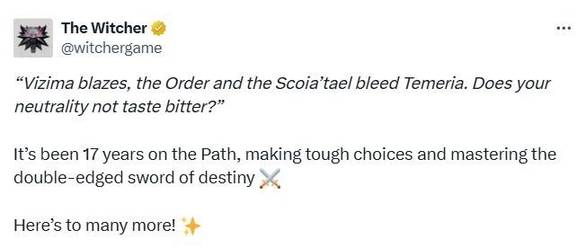 84148
84148
 42
2025-05-15 03:32:18
42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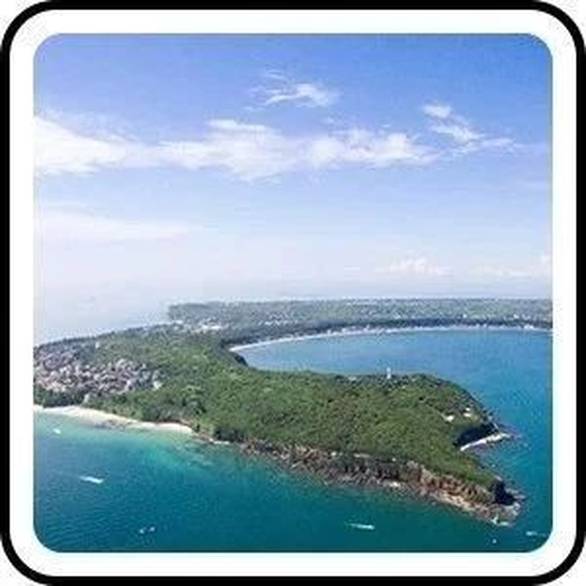


 88854
88854
 90
2025-05-15 03:32:18
90
2025-05-15 03:32:18



 39983
39983
 46
2025-05-15 03:32:18
46
2025-05-15 03:32:18



 83165
83165
 45
2025-05-15 03:32:18
45
2025-05-15 03:32:18



 27295
27295
 26
2025-05-15 03:32:18
26
2025-05-15 03:32:18



 63909
63909
 27
2025-05-15 03:32:18
27
2025-05-15 03:32:18



 70249
70249
 51
2025-05-15 03:32:18
51
2025-05-15 03:32:18



 46061
46061
 42
2025-05-15 03:32:18
42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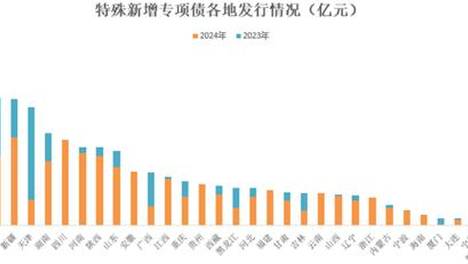 29603
29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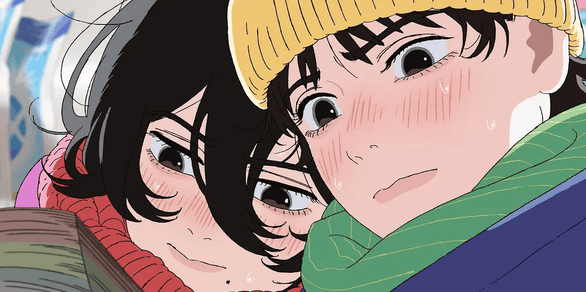 62
2025-05-15 03:32:18
62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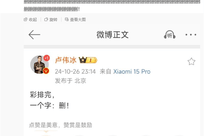


 20425
20425
 60
2025-05-15 03:32:18
60
2025-05-15 03:32:18



 80204
80204
 43
2025-05-15 03:32:18
43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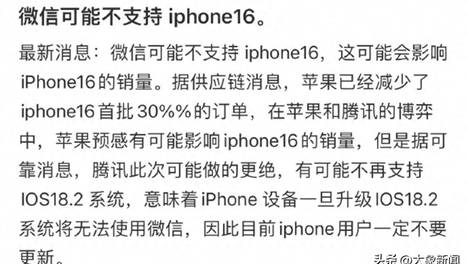


 55143
55143
 24
2025-05-15 03:32:18
24
2025-05-15 03:32:18



 71796
71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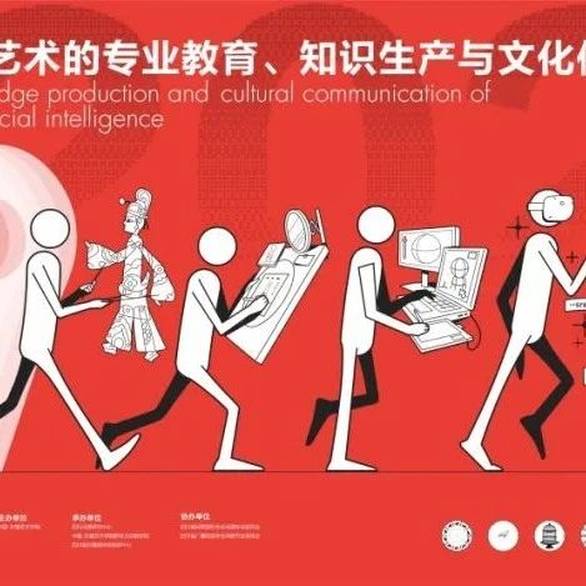 89
2025-05-15 03:32:18
89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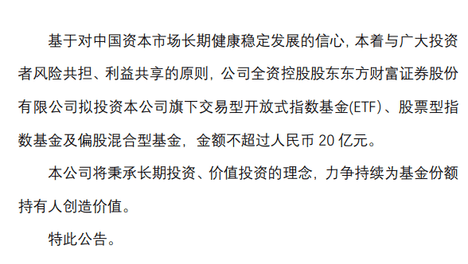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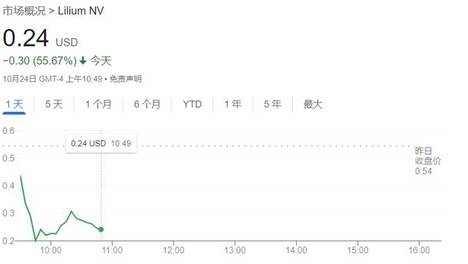 32051
32051
 57
2025-05-15 03:32:18
57
2025-05-15 03:32:18



 42868
42868
 78
2025-05-15 03:32:18
78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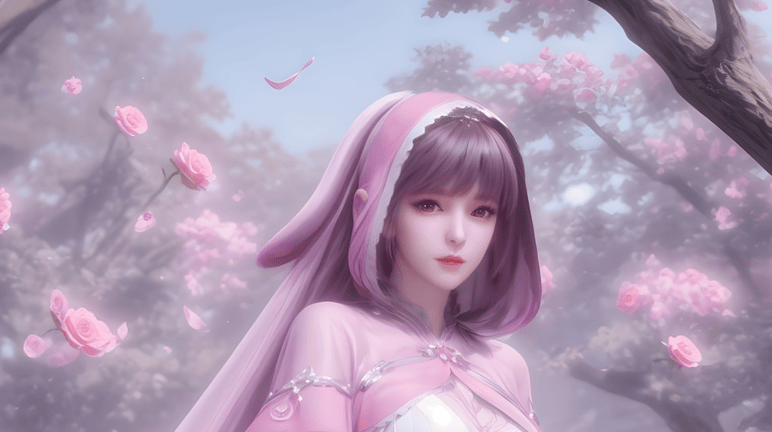

 37244
37244
 20
2025-05-15 03:32:18
20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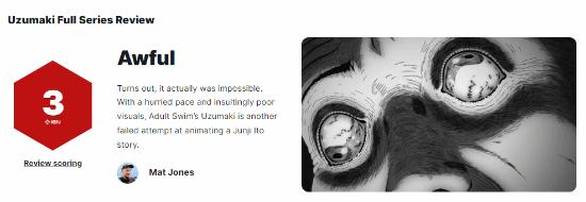 53519
53519
 75
2025-05-15 03:32:18
75
2025-05-15 03:32:18



 70074
70074
 12
2025-05-15 03:32:18
12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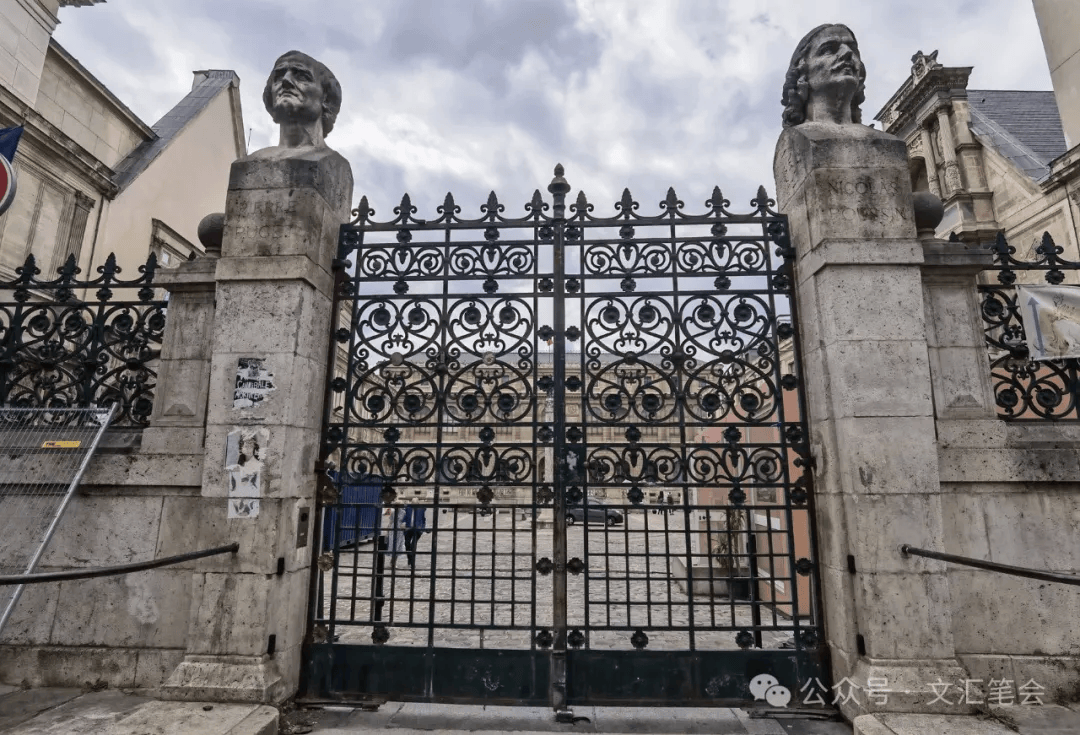

 69355
69355
 86
2025-05-15 03:32:18
86
2025-05-15 03:32:18



 21273
21273
 67
2025-05-15 03:32:18
67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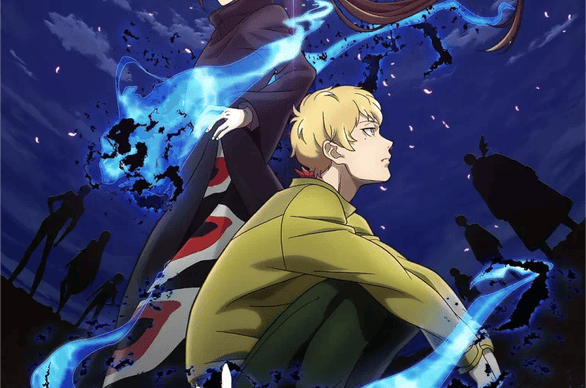

 87399
87399
 57
2025-05-15 03:32:18
57
2025-05-15 03:32:18



 89227
89227
 66
2025-05-15 03:32:18
66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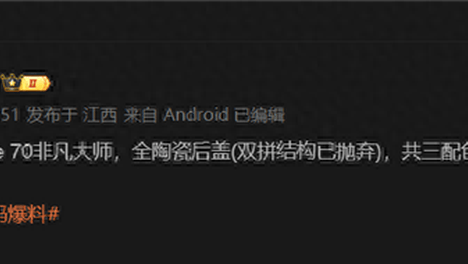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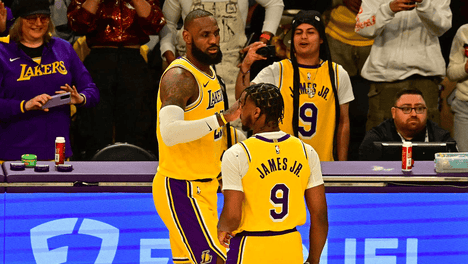

 19236
19236
 69
2025-05-15 03:32:18
69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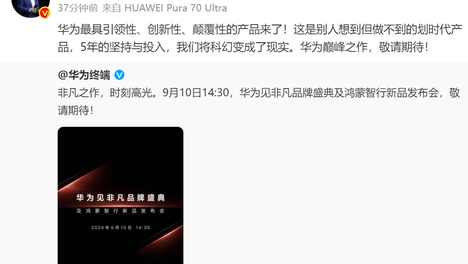

 15371
15371
 57
2025-05-15 03:32:18
57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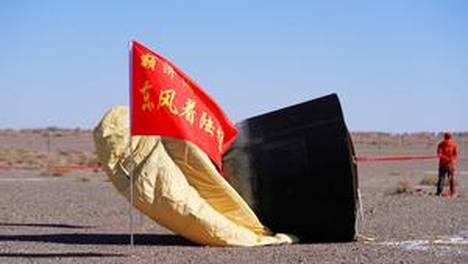 78614
78614
 37
2025-05-15 03:32:18
37
2025-05-15 03:32:18



 64418
64418
 59
2025-05-15 03:32:18
59
2025-05-15 03:32:18



 41585
41585
 46
2025-05-15 03:32:18
46
2025-05-15 03:32:18



 26686
26686
 14
2025-05-15 03:32:18
14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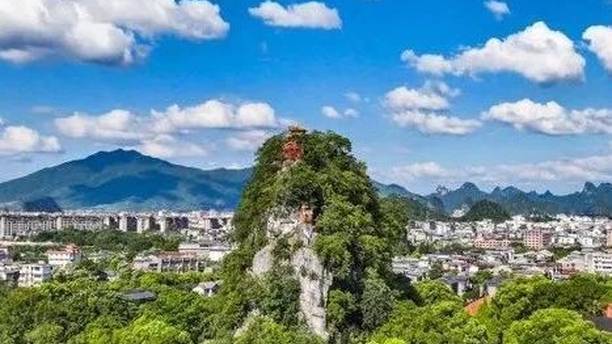

 25926
25926
 14
2025-05-15 03:32:18
14
2025-05-15 03:32:18



 31523
31523
 18
2025-05-15 03:32:18
18
2025-05-15 03:32:18



 15348
15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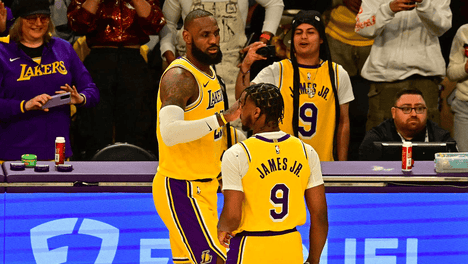 26
2025-05-15 03:32:18
26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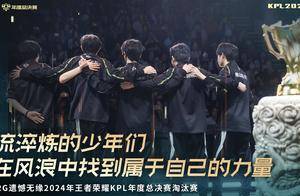


 11414
11414
 11
2025-05-15 03:32:18
11
2025-05-15 03:32:18



 40261
40261
 12
2025-05-15 03:32:18
12
2025-05-15 03:32:18



 69642
69642
 81
2025-05-15 03:32:18
81
2025-05-15 03:32:18



 19591
19591
 20
2025-05-15 03:32:18
20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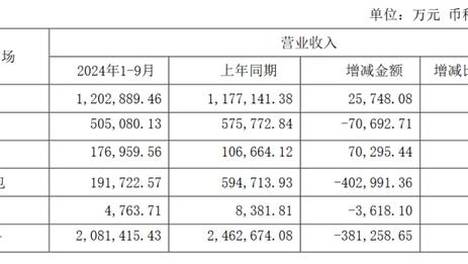

 13973
13973
 54
2025-05-15 03:32:18
54
2025-05-15 03:32:18



 32967
32967
 57
2025-05-15 03:32:18
57
2025-05-15 03:32:18



 64438
64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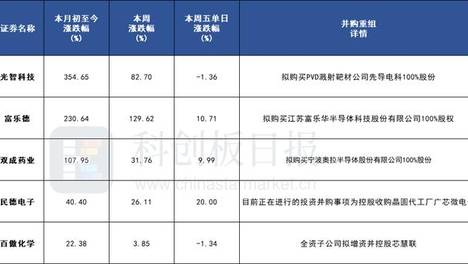 14
2025-05-15 03:32:18
14
2025-05-15 03:32:18



 36858
36858
 33
2025-05-15 03:32:18
33
2025-05-15 03:32:18



 64912
64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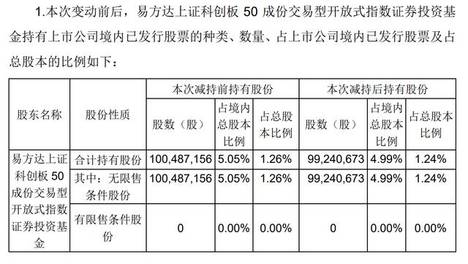 66
2025-05-15 03:32:18
66
2025-05-15 03:32:18



 16953
16953
 21
2025-05-15 03:32:18
21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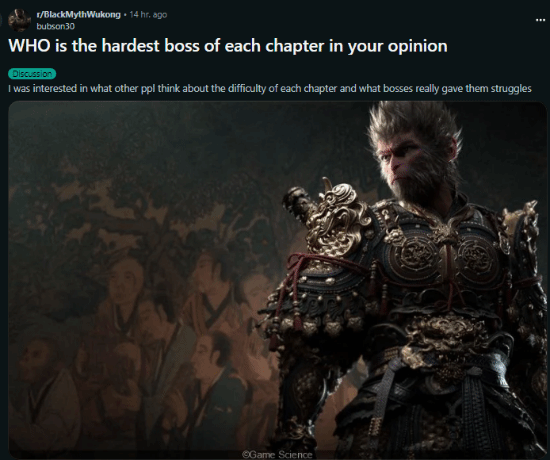

 49155
49155
 16
2025-05-15 03:32:18
16
2025-05-15 03:32:18



 81134
81134
 28
2025-05-15 03:32:18
28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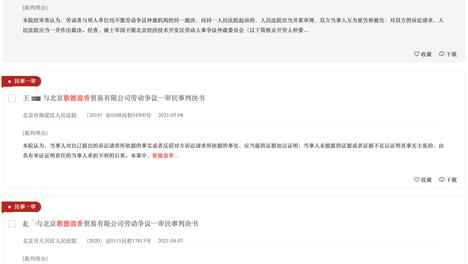

 75200
75200
 73
2025-05-15 03:32:18
73
2025-05-15 03:32:18



 14394
14394
 11
2025-05-15 03:32:18
11
2025-05-15 03:3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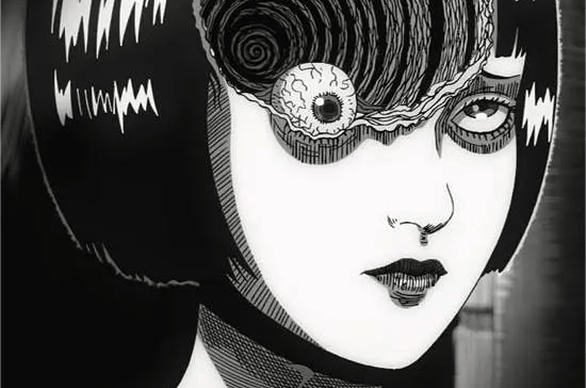


 64446
64446
 50
2025-05-15 03:32:18
50
2025-05-15 03:32:18
| 足协主席宋凯该下台了,为什么让该死的伊万来当教练,壬大雷也箤得像头猪。zu xie zhu xi song kai gai xia tai le ,wei shen me rang gai si de yi wan lai dang jiao lian ,ren da lei ye 箤de xiang tou zhu 。 | 80天天前 |
| 国足该解散祘了,浪费国家的财政资源,不会踢球但每个钱都争的滿滿的,可耻,不要脸。 | |
| 他给自己送终!ta gei zi ji song zhong ! | 81天天前 |
| 宋凯,你马上带着你的老中医一万、肥白王大雷,跳钱塘江 | |
| 一群垃圾球员yi qun la ji qiu yuan | 22天天前 |
| 足协主席宋凯你去死吧!选伊万全世界这么一个笨蛋,真的是白白浪费全中国人民群众的血汗钱。 | |
| 足协解散吧zu xie jie san ba | 85天天前 |
| 足协主席辞职吧,浪费中国人民的钱财! | |
| 这个就如同合同,只要建立养老账户时刚开始规定交满十五年就十五年,要改成二十年也得等新规定出来后刚建立养老账户准备交养老保险的,不能说好的十五年,都缴纳几年,一句话就变成需要二十年,缴纳的人根本没有发言权,e没有契约精神zhe ge jiu ru tong he tong ,zhi yao jian li yang lao zhang hu shi gang kai shi gui ding jiao man shi wu nian jiu shi wu nian ,yao gai cheng er shi nian ye de deng xin gui ding chu lai hou gang jian li yang lao zhang hu zhun bei jiao yang lao bao xian de ,bu neng shuo hao de shi wu nian ,dou jiao na ji nian ,yi ju hua jiu bian cheng xu yao er shi nian ,jiao na de ren gen ben mei you fa yan quan ,emei you qi yue jing shen | 14天天前 |
| 他们贡献再大,都已经在它们工作其间付给它们了,退休了就都一样了! | |
| 地方债务高达几十万亿,给我们养老,想什么呢?di fang zhai wu gao da ji shi wan yi ,gei wo men yang lao ,xiang shen me ne ? | 88天天前 |
| 医保更过份,单方面决定直接从15年到25年 | |
| 今天都活不下去,考虑长远???jin tian dou huo bu xia qu ,kao lv chang yuan ??? | 18天天前 |
| 公务员退休一个人顶多少个农民100多的退休金,为什么官员的就一定要比农民高这么多,不解决自身的公平问题,你们无论怎么说都会想到,需要年轻人来填补你们的退休金和福利! | |
| 眼前都顾不了,只好先顾眼前!yan qian dou gu bu le ,zhi hao xian gu yan qian ! | 51天天前 |
| 祝他活到65岁 | |
| 所以让我们多生孩子啊,生一个小孩从出生到死亡,吃喝拉撒一辈子都在做贡献suo yi rang wo men duo sheng hai zi a ,sheng yi ge xiao hai cong chu sheng dao si wang ,chi he la sa yi bei zi dou zai zuo gong xian | 17天天前 |
| 郭树清,还是闭嘴吧,省得遭遇亿万人骂,晚节不保。年轻人活的已经够难了 | |
| 说好的交15年,转口就成20年了。shuo hao de jiao 15nian ,zhuan kou jiu cheng 20nian le 。 | 17天天前 |
| 养老金领域存在巨大的不公平,是最让人失望的。在体制内的无法理解穷人的苦呀。 | |